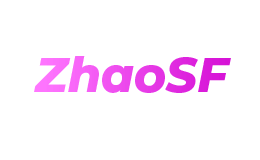
山村小记
我忘了是哪一年去的平山,1991年或者1992年……记得汽车经过一路的颠簸,不知道走过多少条路,先是柏油路,后是碾得不象样的柏油路。后来又走过一段高低不平的山路,终于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叫做小
我忘了是哪一年去的平山,1991年或者1992年……记得汽车经过一路的颠簸,不知道走过多少条路,先是柏油路,后是碾得不象样的柏油路。后来又走过一段高低不平的山路,终于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叫做小觉的地方。
顺着有一点下坡的山路走下去,路上总是有人在和叔叔打招呼,我心里想也许叔叔认识的人多吧。
渐渐的映如我眼脸的是一座小小青色石板桥横跨在一条小河的上方,两边是断断续续的苇子花和青绿的野草,高处的坡上是三三两两的人家,有的人家的屋檐齐着这家的屋基,而有的人家房屋就紧贴在山路的一边,近了,我看到有一位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河里扬起点点浪花,不远处有几只鸭子在水中觅食。清清凉凉的河水从小桥下欢快的流过……
叔叔的家就在不远的坡上,一排五间青色砖房,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是两明间。我看到门前几米远的地方就是往山上走的小路了,四周全是山高高大大的影子。山里人平常农闲的时候只吃两顿饭,中午是不做饭的,显然是为了我们的到来中午加了一顿饭,蒸的白面馒头,拌的丝瓜、烧的茄子、叔叔还把腌制的腊肉拿来了。在深山里平常是没有卖肉的,每家每户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杀一头猪,制成肉干和腊肉,留着过年吃和走亲戚的来了吃,山里的耕地面积少,靠天吃饭,小麦收成很低。即使已经是九十年代了,他们平时也是把玉米面和白面合起来蒸馒头吃,俗称“两掺搅”。我们来了他们特意蒸的白面馒头。吃罢午饭,邻家有个姑娘说是要上山摘枣子,很好客的拉上我一同去,临走的时候叔让我们拿了四、五个筐,我想这能装满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出发了。
姑姑和我还有那个姑娘顺着山路走了上去,已是午后的四、五点钟,虽然是农历的七、八月。但是并不觉得热,山路两旁开满了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小花,一个个扬着小小的脸庞,象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青草和矮树丛参差不齐的遍布在路边,远处山上好像有许许多多的大树。一条蜿蜒的小路象银白的蛇儿在脚下忽隐忽现,越来越远的把小村抛在身后。
终于到了山的深处,山里的空气那么清爽,甚至还有一丝凉意。在一片坡上有许多颗枣树,都是碗口那么粗,象一把把巨大的伞儿,散布在午后的斜阳里,片片深绿的叶子反射着金子一样的光泽,枣儿又大又圆,一边红一边绿,半躲在秘密麻麻的叶子里。在这里打枣是不用竹竿的,姑姑到树下一摇,枣儿“哗哗”的落下来,象雨点一样打在我们的身上,有红透的,还有发一点绿的,滚落在石头缝里,泥土边,山里的空气昼夜温差很大,有的枣儿还带着露珠。捡着湿润硕圆的枣,心中的喜悦是不用说的。又大又圆的枣儿不一会就装满一箩筐,我不禁想起在老家打枣的时候,发动全家人把掉在每个角落里的枣都捡来也不过一篮子枣,可是现在我觉得再装二三十篮子也不成问题,我忽然想起什么问姑姑,这枣树是谁种的呢,姑姑说是山里野生野长的,我心里想野生野长的东西怎么这么饱满和晶莹呢?在平原没有一种果树是不上化肥和农药的,所有的果实好象都要经过人工施肥的,那里有这带着露珠的枣儿呢。?
不经意间抬头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太阳已经微微有点西落了,我们正在一条很深的山壑的边上,大山好像被一把锋利的斧子从中劈开,山的景色因为背光和被照完全不同,这座山因为背光看不太清楚,我正好能看到对面的大山,那是怎样一种壮丽的景色呀,一片绚烂的桔红,一块凝重的深绿、一抹清淡的柠黄,铺积成山的整个颜色,野草、矮树、大树没有具体的轮廓,只有概括的颜色,树下是最原始的黄赫色的一道道沟壑,天然形成,顺着山谷笔直而下,隐到那黑褐的谷底里。放眼望去,坚实巍峨的远山依偎在玻璃体一样空灵广阔蓝天下。这里黑色的山遥望着对面的明亮的山,阴暗衬托着明亮、灰淡衬托着浓艳。夕阳的光芒是那样温暖,明亮,抚爱着连绵不断的山峦,就像慈祥的母亲凝视着怀中快睡的婴儿,一切是那么和谐自然。
静静的听到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们也是在打枣子吗?我环顾四周,我看不到有什么人,只能听到忽远忽近的对话声,……我恍然想到了古人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天空仿佛更远了,山更高了。我静静的伫立在这里,忘了手中的枣儿,忘了我在那里……
带着收获的幸福和快乐,不一会就走到家里。
叔叔问我,“明天我们去摘花椒你还去吗?”
我说:“当然去了。”
叔叔说“花椒很麻手的,你别去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他们就去山上了,我因为摘枣子太累了,睡的太沉没有赶上起来。半响午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看到叔叔和姑姑的手指都变成红褐色的了。而且他们说麻酥酥的,我只是知道花椒能烹饪出那么美味的菜来,不知道它有还么些来历。正说着话,姑姑说邻家大娘请吃饭呢,一快去吧,就在很近的破上。
果然转过一个小坡,我看到了一户人家。土胚的院墙和大门,但是院里很干净,也是一溜眼五间灰色的砖房,檐下有柱廊,柱廊的最西头有一个灶台。紧挨着北屋的东西两边各有土坯的房子,东头屋里喂着一头骡子和一匹马。牲口膘肥体壮,在打着响鼻吃草。
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大娘满脸带笑的走出了,说道“这姑娘都长这么大了,快来屋里坐”
“山里没你们外边好呀!天天没个新鲜的。”
我说“挺好的呀。”
老人格格的笑了起来。搭讪着说过一会话,喷香的饭菜已在一个小桌上摆好。
姑姑说“我大伯不在呀?”
老人说“闲不住,给牲口割草去了。我们先吃吧!”
大概是特意从外边买的大米,蒸的米饭,因为我知道山里是不产大米的。小铁锅里满满一锅菜,尝一口,是晒干的红萝卜干,白萝卜条、好像还有我说不来的什么菜瓜,和着猪肉和粉条顿在一块,滋味不咸也不淡。红罗卜干又甜又香,白萝卜条有嫩又滑……总之,那顿饭我忘了做客人的矜持,吃了满满两大碗。吃完饭,我小声的问姑姑人家在哪做饭呢,我怎么刚才进来的时候,在院里的灶下没看到一点作过饭的痕迹呢,姑姑笑着说,山里人一般很爱干净,作过饭的灶灰一顿一清扫,灶台更是擦洗得干净。在那个时候山里人用水并不是太方便,虽然每家都装上了自来水,可是居住在山坡上稍微高一点的人家,自来水是流不上去的,叔叔家水管这几天还是滴滴嗒嗒的,更别说他们在坡上了。在这么有限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