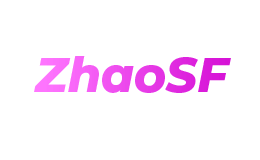
我读顾城诗(一)
顾城被誉为“童话诗人”,是朦胧诗派里的一位天才的诗人。他前期的诗歌具有浓厚童话色彩。他诗歌童话色彩的特点的形成深受他儿时一些经历的影响。在他诗歌所营造的童话氛围里,色彩美和意象美两点尤为突出。但当他的
顾城被誉为“童话诗人”,是朦胧诗派里的一位天才的诗人。他前期的诗歌具有浓厚童话色彩。他诗歌童话色彩的特点的形成深受他儿时一些经历的影响。在他诗歌所营造的童话氛围里,色彩美和意象美两点尤为突出。但当他的童话梦破碎后,潜藏在他灵魂里的死亡意识开始涌现,使诗歌中的童话色彩也不复存在。我要用心中的纯银
铸一把钥匙
去开启天国的门
向着人类
——顾城
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诗歌潮流,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但是他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朦胧诗的三个主要代表人,北岛,舒婷,顾城,诗歌风格各异。北岛用深沉忧郁的笔调去控诉现实社会,舒婷用明朗清澈的语言去呼唤灿烂的明天。顾城则是以纤弱,纯净的诗风格外引人注目。他以孩子的角度来观照这个世界,将世界塑造成他心中的童话王国。舒婷曾把一首名为《童话诗人》的诗送给顾城,诗中写道:“你相信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为了童话里幽蓝的花。”“童话诗人的称号,顾城当之无愧。后来有评论家也称他为“唯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顾城的诗歌之所以那么有灵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诗歌充满了童话色彩。
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诗人也是如此。顾城是一个早慧的诗人,8岁的时候就从“雨滴”中悟到了诗的存在,觉得“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
(1)顾城的诗歌被认为是纯净的,幻想的,天然的。他的诗歌语言,形象都偏向于“回归自然”。他童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以及生命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张捷鸿在《童话诗人:别无选择的定位》里谈到:“童年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而作家的创作经历反过来也或多或少的修正和补充了作家的童话经验,很多作家的“童年经验”本身就带有文学创作痕迹,它既是作家解释创作动因的根据,也是作家,对创作‘血统’的验明正身。”
(2)十二岁,顾城的父亲顾工被下放,顾城也随父亲去了一个叫火道村的村庄。在那儿,他与自然为伴,倾听大自然的语言,从中积聚了很多诗歌创作的素材。顾城对大自然是疯狂热爱的,甚至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后来多次谈到那个时期生活是时,他都会说:“我是一个放猪的孩子,没有受过教育。”顾城将以后所有的生命都有意识的定位到了这个时期。他相信在他的诗歌的最后,城市将消失,最终出现的会是一片牧场。在火道村的时候,顾城读了J。H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成为影响他人生最大的一本书。小顾城一夜之间爱上了自然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在自我/大自然的二元关系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和谐和完美的联系。”
(3)他开始在诗歌中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他用“紫云英”,“松塔”,“雨滴”,“小花”等意象寄托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正是因为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忘我于大自然的生活态度。当他再次回到城市,他感到孤独了,因而变得沉默了,“十七岁我回到城里,看到好多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人都说一样的话,你说得不一样,他们就不懂”。
(4)诗人后来又说:“因为畏惧说话,所以我变得滔滔不绝。”
(5)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东西诗人将它寄寓在诗中,强烈地想要写作,常常都意味着拒绝生活。但在诗的王国,他是自由的。“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小春天的谣曲》)。顾城一直认为安徒生是他的老师,他们都曾做过笨拙的木匠,都保持着一颗不变的童心。“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给我的尊师安徒生》)。“花”和“梦”都是遗落在童话里的珍珠,只有拥有童心才能真正体会它的“纯美”。
顾城的童心表现为他是拒绝长大的,这种心理定势左右着他一生的创作与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他常常是以孩子自居,用孩子的角度去描述这个世界。“我是一棵长不大的小草/偶尔能触一下阳光的绒毛。”(《门前》)。他的诗歌里还有“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简历》)。他并不是“长不大”,也不是“没有长大”,而是他自己从心里上就不想长大,长大之后又拒绝成熟,坚守着自己的童话理想,将自己永远与其他的成年人划清界限。他一直在做自己的童话王国中的“王子”。他欣赏李贽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观点,他自己还强调“童话”的“童”是李贽“童心说”的“童”,是指未被污染的本心,而不是指儿童幼稚的心。他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里写道:“最后在纸角上/我还要画下一个树熊/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孩子的呓语在他的诗中被写得那么自然。诗人与诗中的“树熊”达到了异质同构的效果。将“我”的理想通过“树熊”的角度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浆果一样的梦”,“很大很大的眼睛”这些都只有孩子的心才能去观照。纯净,无私的“梦”通过这些意象传达到每一人的心里。
顾城的童话并不是完全纯净的童话。他的童话里蕴含着悲剧的情结在里面。“悲剧情结本质上是悲剧时代异化的产物。”
(6)时代的悲剧也是他“童年质情结”形成的一个原因。十年文革是民族的悲剧,更是一代青年的悲剧。而顾城正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十年的阴影在他生命中如梦魇般无法抹去。顾工在《顾城的诗》里回忆了顾城童年的一个片断:“在文革时期,有人在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满了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绕来死死的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叶的缝隙中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像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来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澈越的声音,只想去看天籁的世界。”此后,顾城变得孤僻了,想离开现实,躲进了乌托邦式的童话世界。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生的理想性在他的心里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他的希望在不断破灭。“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想把破灭宽恕/破灭从不把幻想放过。”
(7)(《幻想》)在他眼里不管什么美好的东西最终都无法逃离破灭的劫数。他觉得:“人的每一个希望都要破灭,都要变成干枯的花瓣。”顾城童年的悲剧情结在他诗歌的童话色彩上更添加了一层凄艳的悲剧色彩。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切入现实,展示世象
下一篇:还要继续在“红袖”中写作吗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