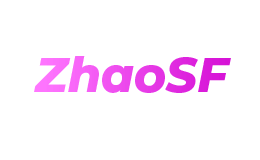
干净的房间
母亲说我的房间是一个堆满杂物的大垃圾场,每次她用手使劲旋开房门栓的时候,堆积在门后的木头画板和颜料盒都会争先恐后得往前挤,然后掉出来,撒的满地都是。立在墙角的那把古典吉他“咣当”一声倒在木地板上,堆叠
母亲说我的房间是一个堆满杂物的大垃圾场,每次她用手使劲旋开房门栓的时候,堆积在门后的木头画板和颜料盒都会争先恐后得往前挤,然后掉出来,撒的满地都是。立在墙角的那把古典吉他“咣当”一声倒在木地板上,堆叠在粉红沙发里的衣服似乎吓了一跳,全部颤颤悠悠地往地上滚。在铁路南苑小区,我独自拥有一间足足有一百平米的单人房。但是我的房间却从来没有整齐干净过。那张白色宽敞的书桌上摞着像一座小山丘那么高的书和本子,信封和打印纸铺的满桌都是,各种各样的笔散落在信封,纸张,甚至书本里。桌子上还摆满了各式各样我喜欢的小物件,比如卡通玩偶和一堆儿花花绿绿的饰品盒。假如一枚扣子,或者一只更小的戒指掉在这个桌子上,那么,基本等于石沉大海了。在我的书桌上找东西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
我从来不爱打扫屋子,以至于木质地板卷起一层层灰卷儿,书桌和台灯上落了厚厚的尘土。夜里盖过的被子也是翻卷铺陈在床上,从没有叠起来的时候。之所以养成这样的习惯,源自于我对艺术家的理解。在我的意识当中,觉得房间杂乱无章才能显现出一个艺术家的不羁和个性,那些撒的满地都是的颜料和墙上贴的杂七杂八的招贴画总被我视作艺术气息浓厚的证明。所以,每当母亲对我脏乱的房间嗤之以鼻的时候,我都会挺着胸脯告诉她,艺术家就是这样子的。
可是,孙启娟却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孙启娟是我同在艺术学院的同学,她是一个哑巴,也是一个聋子。她的父母是工厂里的下岗工人,父亲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了,母亲一个月只有一千块钱的工资,因为要供她上学家里欠了债,但是仍然没有能力令她读完所有的学期,大二那年,她就辍学了。
上学的时候,孙启娟接受过我们班所有同学的接济,每个季节,我们都会把那些不赶潮流的衣服收拾出来,送给她穿。
有一年冬天,我的母亲在橱子里拿出一件她年轻时候穿过的驼色大衣,因为生我以后腰身发胖再也穿不下去,便想着要打发给人。我瞥了一眼这件五十年代直筒型洗的有些发白的大衣,想也没想就说:“给孙启娟得了。”于是,这件大衣就成了启娟的一件最好的衣裳。孙启娟穿衣服,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我从来没有在夏天时发现她的衬衣领子开过一个纽扣,不管多热,她的袖口都死死地钉在一起,裤子笔直的外扎住衬衫,笔挺笔挺的。母亲那件驼色大衣穿在她身上似乎缩短了她的身高,衣角好像要拖到地上似得,肩膀也松松垮垮,她又硬要从上到下把每个扣子都一个不拉的系好,瘦小的身躯套在里面,更像是被装进了铁桶里。每次穿这件大衣,她都把头昂地高高的,腰板挺地直直的,以便能撑起这件不合体的衣服。
大学时我第一次去孙启娟的家,那是一间用破砖瓦堆摞起来的小平房。她的母亲就在用石头垒起来的灶台上做饭。里外总共一间屋,还不足四十平米,家具也很简单,只有一张写字台,一张床和一个立柜。衣橱就在床边上,饭桌摆在大门口,门边杵着几把板凳子。房间里都是石头地儿,蚂蚁就在上面跑来跑去。
孙启娟把我让进屋里来,自己跑到屋外帮她母亲做饭。她家地方窄,家具又少,我一时没找到坐的地方,只好在地上来来回回的走。走了一会儿,我就发现剥落了皮的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油画,油画的画框上没有一丝灰尘。衣橱也很光亮,我把脸贴上去,能映出影子来。写字台上摆了一流笔筒,哪些是装毛笔的,哪些是装铅字笔的,哪些是装铅笔的,都分的清清楚楚。老式台灯立在床头,看上去跟崭新的一样,我的手摸上去能印出一个指纹印来。床上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那样板正,褥子也像是刚洗过似得。
我走了这么一圈,似乎感到她的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小屋变得大了起来。那些挂在墙上的素描稿沐浴着阳光,上面的人儿似乎要飞起来。画板子直立着站在地上,每一张画都被夹子整齐的夹在一起。
她辍学之后,我有两年时间没有见过她。再一次见她,是在《齐鲁晚报》上的一个新闻版面里。当时,在那版名叫《事实新闻》的板块里,有一侧带图片的事实新闻,图片上是我的同学孙启娟,她正举着一张工笔人物画站在领奖台上。照片上,她的表情非常严肃,紧紧皱着眉头,眼睛定定的盯着前面的摄像机。可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母亲脸上却洋溢着笑容,皱纹在她的脸上绽开,像一朵花儿。那个新闻的题目叫做“聋哑女艺术家”。
从这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突然收到孙启娟的一个短信息。她问我有没有空,想约我聚聚见个面。我说那就约在历下大润发的肯德基店里吧,这个地点距离我们两个的家都很近。那天我起的很早,换了一套新衣服,当赶到大润发的肯德基店里时,却看见孙启娟已经坐在肯德基的圆桌上喝饮料了。我走过去,发现她穿了一件掉了毛的绒线衣,雪白的脖子衬托得绿色绒衣的颜色也青翠了许多,乌黑的头发像缎子一样松松散散盘在脑后,侧着头,晨光就撒在那长长的卷曲的睫毛上,手里拿着已经喝下去一大半的饮料杯子。
孙启娟见了我很高兴,赶忙拉着我的手坐下,然后掏出纸和笔,要跟我“说话”。我看了看她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那也是我在学校里送给她的。这款“摩托罗拉”曾经也是我母亲的物件,我母亲在国内刚开始流行用手机这种电子设备的时候曾一共换过两部手机,一部是跟砖头那么大的“大哥大”。另一部就是这款“摩托罗拉”。这是一部直板手机,大约有一个人的手掌那么大,屏幕很小,而且没有颜色,基本上除了发信息和打电话就没有其他功能了。这款手机我母亲用了很久,我13岁那年,她又换了一个更好一些的,就把这部淘汰给我了,目的是想让我能随时跟家里保持联系。我考上大学后之前就已经不再用这部手机了,其一是因为它样子已过时,其二是我在素描培训班学习时摔过两回。第一回,是搬着书架子从培训班的楼梯上下来。当时,我和几个同学正抬着书架,随手就把手机撂在架子上面。培训班在五楼,当我们从楼梯的弯道上拐弯时,手机顺着窗户沿儿就掉下去了。那个年代出产的“摩托罗拉”质量很好,即便是从五层楼上摔下去,也照样能打电话。只是此后,这部手机便没了机壳,绿色的机电子板光秃秃的暴露在外面。第二回是去淄博写生磕在了石头上,屏幕也掉了下来,用塑料胶带缠几圈,也还是能用。
这部手机我上大二的时候送给了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