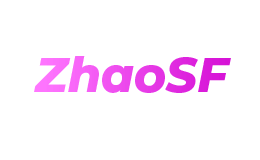
那天,卧牛山的眼睛红了
在鲁西南大地上,有一片不大的山区。这里的山和几十里外的其他山不同,那些山的山石都是可以烧石灰、做水泥的青石,这里却是只能做石料的白砂石。所以,这片地方被称为白石山区。白石山区的几座山里,最有名的要数卧
在鲁西南大地上,有一片不大的山区。这里的山和几十里外的其他山不同,那些山的山石都是可以烧石灰、做水泥的青石,这里却是只能做石料的白砂石。所以,这片地方被称为白石山区。白石山区的几座山里,最有名的要数卧佛山和卧牛山。
卧佛山在山区的中心。此山因形状酷似一座仰卧的大佛而得名。山上有庙,还有戏楼,过去每逢卧佛山庙会的时候,都要唱五天大戏。
卧牛山在山区的东南方。山的东面南面就都是平原了。此山也因形得名。从山的西南方向看去,恰似一头巨大的水牛俯卧在那里。牛头向东偏南,牛屁股向西偏北。千百年来,这座山就以卧牛山名世。牛头向阳的一面,有一个石穴,据说是卧牛的眼睛。老辈人有一个传说,如果石穴——也就是卧牛的眼睛哪天红了,这里的人就要遭遇巨大的灾难。
本来,传说就是传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传说竟然在这年的秋天应验了。
故事发生在卧牛山西南二三里处一个小山村,村名也叫卧牛山。
一
这天是公元一九七三年农历的正月初十。下午,卧牛山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向东从县里开完三级干部会回来,在崎岖的山路上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走着。那路很不好走,七拐八弯,凸凹不平,就像是人生的旅途。不知怎么的,王向东忽然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本村过去是十几里外一家大地主的佃户村之一,现在则是全公社最小的行政村,也是最穷的一个村。全村只有两个生产队,不到二百口人。大约一百多年前,那家地主占有了这片山地,因为这里的地薄,收的租子也少得多,每亩只要六十斤粮食;一些贪图地租便宜的穷汉来到这里,慢慢地扎下了根,形成了小小的村落。后来解放了,土地先分给各家各户,后来又归了集体,但终究还是没有摆脱一个“穷”字。每年过了年不久,三分之二的户就要等着救济粮度日。村里的地虽然不少,但因为都是山岭薄地,赶上好年景,每亩也只能收个二三百斤。如果大旱,就会颗粒无收。在这样的村里当干部,想靠搞好生产出人头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可就这样子熬下去,又怎么能让人甘心呢?
王向东是这个村里唯一的一位高中生,也是全公社五十个大队支部书记中唯一的高中生。在他上高二的时候,“文化革命”爆发了。他和同学们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并被选为群众组织“东方红”的头头,他也把原名“王进东”改成了“王向东”。本来他是想改成“王卫东”来着,但那名字已被别的同学捷足先得,这才改成“向东”。后来,因为他不赞成对所有“当权派”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戴上了“保守派”的帽子。拥护他的人成了少数派。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相反,认为和他们对立的人是“极左派”,并不是真正的“造反派”。两派之间势不两立,今天文攻,明天武斗,在翻来覆去的斗争中,他也成了全县最有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造反派”得势了,他的对手们成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委员,更多的是担任了各单位的革委会主任。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随着当年征兵,到了部队。
在部队,他有文化、能吃苦,又处处注意积极表现,不到一年就入了党。第二年,眼看就要提干的时候,本县却有人向部队写了揭发信,说他是派性组织的头头,参与过多次打砸抢。结果,不仅提干的希望破灭,军装也不能再穿了。他提前一年,随着当年退伍的战友离开了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写的揭发信,他到底也没弄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文革中的对立面。他愤愤不平:真正搞打砸抢的都他娘的在县里当官了,我这没搞打砸抢的却被清算,真理到底在哪里?
他曾一度悲观失望。看来自己这辈子就要这样“怀才不遇”了。
可是,就在他回来不久,风向又变了。这时候,开始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山东这地方的“一打三反”,是由新改组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新改组的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以及与造反派做过斗争的群众代表组成,原来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被清除出去,反过来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这年冬天,公社在他们村的山岗上搞“大会战”。会战指挥部里要找一个有文化的人办简报,村里人推荐了他。他写的那些富有煽动性的宣传文章、顺口溜,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赞赏。
接着,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他所在的卧牛山大队连他在内只有五个党员。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老全年纪大了,用公社驻队干部的话说是“老牛歪在墒沟里——打一百鞭不起毛”了,于是,他被提名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形势的变化使他萌发了新的希望。他把担任支部书记看做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文革”初期那些在运动中“跳高”的人,都已经重重地摔了下去,他有时暗自庆幸:那时候自己的一派没有占了上风,反倒成了好事。其实,群众组织哪里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要想整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他知道,后来让他担任了支部书记,意味着“文革”中的是非一笔勾销,他不用再背负那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如果干出点儿名堂来,说不定还有继续上升的机会。即便坐不上“直升飞机”,来他个“拾级而上”也不错,反正自己还年轻。他不止一次盘点过全公社各大队的主要干部们,觉得如果全公社选拔一个脱产干部,只有自己最符合条件。
现在这年代,许多事都没有定数。说起来,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子并不大,可是因为当了典型,竟然一跃成为中央委员、省委副书记,今后说不定还能进政治局呢;还有吴桂贤,只是一个纺织工人,也成了中央委员、陕西省委副书记。其他还有很多当了省地县的官员。我王向东如果也有机会,当个什么也应该比他们更能胜任吧?
可是,只有成为典型,最好成为全国的典型,才有可能遇到那样的机会。问题是,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小山村,搞生产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大会上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关键是在本村,想要“抓革命”也很难:全村连一个四类分子也没有。“文革”中,这里虽然也随大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谁都知道那是做做样子的,这里实际是世外桃源,没有什么派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相信这话是当然的真理。但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阶级斗争应该怎么抓?他回想他熟读背诵的语录,终于找到了答案:“除了沙漠,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