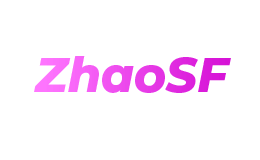
自省
一好长一段时间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用写作打发空闲时间。从某些角度看,我是不适合写作的。比如我的情商不高,想象力单薄,文字处理能力不强。虽然读过一些文学作品,背过一些诗词歌赋,但基本忘光了—对
一好长一段时间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用写作打发空闲时间。
从某些角度看,我是不适合写作的。比如我的情商不高,想象力单薄,文字处理能力不强。虽然读过一些文学作品,背过一些诗词歌赋,但基本忘光了—对,现在我的记忆力衰退明显。
我编了一本小册子,我是以散文来定义的,但在作家专家面前什么也不是,“写得太实了,没有空间感”“缺乏灵动感觉”“改行写小说吧”。除了写小说这一条,其他评价我心服口服。小文章都写不好,哪能写好小说呢!
然而我还在写,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每天有空了想的是,今天能写点儿什么;回想回味的,是某件事、某个人、某句话、某篇文章是否打动了我。
想来想去,我还是想说话。想把心里想的话以字为证说出来。标志我在某天想的是什么、说了什么。
二
写作肯定有技术。我没有技术,只有纪录。但我比父亲好得多,认识的字多些,多数还会写。
会写字就会写作,这是最低层次、最浅水平的写作。与《诗经》里记录的最早文学好有一比。当时人们随口而吟的,并不是想留下什么经典。但一个有心人记录了,流传下来,就成了典籍。再说,那个时代,再没有什么文化作品。
我如同原始人一样,记录下当时劳动时为了协调步调而发出的“哎哟哎哟”。
技术是后来生活安逸之后有文化的人专门研究的。他们从种种记录里分门别类,找出相同或不同的作品,然后归纳出文学方法来。他们在前人文学的基础上裁剪、整理,或者进行新的创作。便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诗、词、曲、赋等等。
三
生活肯定是创作的源泉。
几千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演变,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营养和素材,才有了我们今天敬仰的《左传》《史记》《四书五经》,有了文学的高峰唐诗宋词元曲,有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有了传扬千古的大批文学巨匠。
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文学,也离不开生活。但凡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生活的浸润,都是作者从生活里撷取的片断。只不过,这种撷取是有选择、有技能、有窍门的。
我知道这些,并不代表我能做到这些。言易行难,永远是这样。我始终认为,人是有差距的,生活是有距离的,文学作品也应当是生活及作者千差万别的呈现。“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是位诗人朋友重复的名言。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只能记录我所知道、我的写作能力能够把握的这些东西。我只能写下自己想得清楚、基本明白的一些感悟。
境界决定作品高度,这是完全正确的。
四
懂得差别,承认差别,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态度。对于认识到的差别,以及差别的原由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缩小差别,改进自己。
同时也清醒地知道,每个人的习惯与能力都是在一定范围确定的,不是想怎样就能怎样的。改变自己的困难,提高自己的障碍,可能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或许,这个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
特别在写作上。对文字的敏感,都社会生活的见解、对文学体裁的把握,不是有了想法就能达到目标的。有些时候,不得不承认在某些领域,都有天才。
李白、杜甫、苏轼他们肯定有天才成分,否则,在那样的环境下,在没有前车可鉴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创造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同理,大大小小的文学老师们,都有他们独特的对于文化的理解与对文学的感觉。因为有这种东西,加之他们的执着,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们如同我夜晚站在戈壁滩上仰望看到的繁星。当然我就是戈壁滩上那枚沉默寡言的小石子儿,我只好记下风过戈壁的声音、沙过戈壁的掠影、雁过戈壁时的鸣叫,以及人过戈壁时的脚步,
还有雨落戈壁的淅沥、雪落戈壁的冰冷。
五
我只能做到这些。所以我从来没有失落。因为我尽力了。
我不会做力所不逮的事情。我要写作的快乐,不愿意让写作成为生活中的压力。
我不愿意执着。如果我觉得实在没有写作对象,确实没有写作想法的时候,我会欣然放下。
但现在,我还没有放下的思想,我觉得,我想说的话还很多。
还有些人物事件需要我的记录。比如二哥就说让我写写他,至今我还没动笔。我想等我想好怎么写了再写他。
我得为我笔下的字负责。
六
有人说,写作者,有的可以称为作家,有人只能说是写字匠。深为其然。自觉得,能当个打工的小匠人,也是很荣幸的。父亲是个泥水匠,小的时候看他用泥板把活好的稀泥一下抹到墙上,光光的,被别人羡慕,受乡邻尊重,自己非常光荣;母亲是个裁缝,几个村子里唯一的会踩着缝纫机做衣服的人,也是让我极其得意的。现在,我要能做个文字匠人,若能留下让儿子得意的事情,便是很圆满的了。
我感觉,还是读书太少、记忆太差阻碍着我写字道路上的速度,这是需要进一步克服的。
2015年1月27日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下一篇: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相关文章
